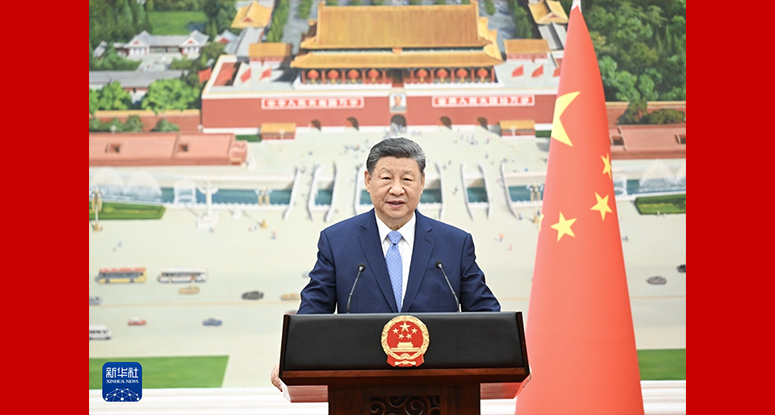颍川,苏轼兄弟“夜雨对床”的终极约定
迄今为止,我还未到过许昌,也就是苏轼那个年代的颍川。之所以向往许昌是因为颍川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心灵上实现“夜雨对床”夙愿的终极之地。
要说“夜雨对床”,就必须说苏辙和苏轼,这对人世间感情最深灵魂相通的兄弟。
苏轼是他那个时代的名人,用今天的话来讲,是“顶流网红”。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被贬边僻,抑或是在贬谪路上,他都如此万众瞩目。他刚到贬谪地惠州,就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从此民间就有了“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流传。他获赦北归,一路上,人们争相一睹这位大名士的风采,引得苏轼一阵惊呼:“莫看杀轼否?”
当然,为与苏轼做邻居而热情向他伸出橄榄枝者就更多了。初步统计,记载苏轼买地(含欲买之地)就有十余处。大家耳熟能详的,当数与王安石的“金陵(今江苏南京)之会”。二位昔日政见各异的对手,在这一刻握手言和了。王安石不仅赞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还热情邀请苏轼在金陵买地筑室,做他的邻居。苏轼写诗回赠王安石:“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被徽宗皇帝大赦终获“任便居住”的时候,先于苏轼获得诏命的苏辙就直奔颍川而去,因为他在那儿有些田产,儿子孙子大多数人都在那里等着他。迟于苏辙三个月而获诏命的苏轼,原本谪居海外就交通不便,所以当苏辙到达颍川时,苏轼还在北归的路上。
一路上,苏轼屡屡受人之邀而改变卜居地的想法,是“风土安好”的舒州,还是“缘在东南”的杭州,或是“此邦君子”的常州,他一直犹豫不定。苏轼写信给友人钱世雄:“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可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
我想,苏轼当时最想去定居的地方,当然是颍川,那里有他情同手足的老弟,他们有“夜雨对床”的约定还未实现。可是,历史总爱与人开玩笑,兄弟俩还没见面,便阴阳相隔,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
苏轼不是不想与苏辙待在一起,他始终记得当年他与弟弟苏辙“夜雨对床”的约定。那是他们在京城怀远驿,为迎接制科策试朝夕相处时,兄弟俩有感于韦应物诗“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乃相约功成身退,为闲居之乐。这便是他们“夜雨对床”之约的起点。
制科考试的结果,世人都知道。苏轼入最高等级:三等,这是北宋以来获此最高等级的第二人,苏辙入四等。可以说,“夜雨对床”之约为兄弟俩取得良好成绩提供了精神动力。若干年后,当一个又一个打击接踵而来的时候,“夜对之约”便成为兄弟俩心中的一盏明灯,支撑着他们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尤其是苏轼,“夜对之约”更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可不是么?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愿辞去身上的所有官职,只为换取苏轼的不死。《宋史》这样评价苏辙:“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轼则在狱中向苏辙深情表白:“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与苏辙,也曾有过几次短暂的“夜雨对床”。曩时,苏轼倅杭州,取道陈州。其时,苏辙为陈州学官。兄弟俩相会后,一同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访恩师欧阳修。一路上,苏轼与苏辙游山玩水,饮酒赋诗,兄唱弟和,不亦乐乎。绍圣之初,两兄弟皆被贬,当苏轼行至梧州,听说苏辙就在前面,便追了上去。兄弟俩在藤州相见,并一路行至雷州半岛。他们故意放慢脚步,拖延时间,只为兄弟俩能够多待一会儿。时至今日,沿途留下了他们不少遗迹。直到苏轼将苏辙送至贬所雷州衙府报到,苏辙将苏轼送至徐闻县递角场。兄弟俩在海边跪地泣别,苏轼才渡海远赴贬所海南儋州。这一别,竟成兄弟俩的永别。
但是,以上这些,都不是苏轼与苏辙最终追求的“夜雨对床”。在怀远驿,他们相约的是,当功成名就时,一起从“庙堂之高”退下来,处“江湖之远”,回归故里,放浪乡野,做个自由自在的闲人,而终老。
此时,苏轼与苏辙都明白,故乡眉山是回不去了,他们的“夜对之约”只能在“他乡”实现。好在,苏轼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辙也把他乡作“家乡”。“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西望故乡,犹数千里,势不能返,则又曰:‘姑寓于此。’居五年,筑室于城之西,稍益买田,几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苏辙《卜居赋》)。那个地理上的故乡,它的象征意义,在苏辙这里,就由颍川来代替吧。
所以,颍川,差一点便成为兄弟俩“夜雨对床”的终点。
当苏辙来到颍川,便向哥哥发出了数道迫切的邀请,要苏轼全家来颍川定居,以实现他们的“夜对之约”。清代袁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记叙了当时的情形:“子由有书来促归许下(今河南许昌),甚急。念老境庶几,不欲作两处,遂决计从江溯汴,于陈留陆行至许。”苏辙言辞之切,让苏轼都忍不住要在信中告诉友人,“某本欲居常,得舍弟书,促归许下甚力”(苏轼《与胡郎仁修》)。苏辙觉得仅凭自身一己之力尚且不够,又拜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辙在给辨才大师的信中说,“家兄子瞻以书告曰‘不如至吴中’……子瞻昔与辨才师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见”(苏辙《与辨才大师贴》)。
苏轼也不是没考虑过举家前往颍川,与弟弟一家同住,甚至他多次有过此种想法。他向孙叔静说:“渡岭过赣,归阳羡,或归颍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又作书与李之仪:“又得子由书及见教语,尤切至,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廿八(公元1101年8月24日),苏轼卒于常州,兄弟俩没能在颍川会合。
其实,即使苏轼健在,他也不会去颍川与苏辙同住。苏轼的想法屡屡变化,“行计屡改”“行计南北,凡几变矣”(苏轼《与子由弟》),除苏轼“不忍更以三百指诿之”(苏轼《与黄师是》)外,更重要的是,此时朝廷风向有变,新党已露反扑之态。“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苏轼《与子由弟》)。事实证明,苏轼的判断是正确的。
苏轼是执着甚至固执的,但在选择定居之所问题上,他又是折中和圆润的;同样,苏辙是多情而感性的,但面对朝中时局的微妙变化,他又是理智和理性的。因此,在建中靖国元年那个夏天,苏轼和苏辙二兄弟都放弃了在颍川相会的想法。这是他们面对残酷打压而向现实世界作出的退让。
好在有苏辙!在颍川,他完成了与哥哥心灵上的“夜雨对床”。
苏辙定居颍川十年,闭门谢客,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著书立说,给后世留下了《诗传》《春秋传》《栾城后集》《栾城应诏集》等皇皇巨著八十四卷。
这些著作,无一不是“三苏”学说,特别是苏轼之说的一脉相承。《宋史》赞其云:“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苏辙的这些巨著,让唐宋八大家之“三苏”,更立体,更丰满,也更有说服力。
也是在颍川,居许十年余的苏辙有感而发,写下了有名的《卜居赋》,文中他说:“今子瞻不幸已藏于郏山矣!予年七十有三,异日当追蹈前约。”苏辙的意思,他要跟随哥哥苏轼的脚步,死后同葬于一处,以另外一种沉默而静美的方式,再续和兑现“夜雨对床”的约定。
好在有苏过!他替父亲苏轼完成了与伯父苏辙的“夜雨对床”。
苏轼辞世后,苏过带领全家投奔远在颍川的苏辙。宋人笔记载,“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
当苏轼远谪惠州和儋州时,年轻的苏过就忍受着离别之苦,抛妻别子,陪同年迈的父亲漂泊岭外。苏过随侍父亲,时与唱和,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在颍川,又与伯父苏辙比邻而居,营湖阴地数亩,自号“小斜川”,著有《斜川集》二十卷。这个被后人誉为“小东坡”的苏过,是苏轼三个儿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
苏过替父完成“夜雨对床”的心愿,是名实相符的。
好在有姜唐佐!他不负东坡所望,科考及第;并以不懈之力促成恩师留下的断诗接续。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姜唐佐从学于苏轼。苏轼遇赦离琼时,勉励姜唐佐努力学习,还赠诗一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并对他说,等你科考登第后,我就为你补齐这首诗。姜唐佐谨记恩师教诲,怀揣补诗梦想,游学广州,科考得中,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只可惜,此时的苏轼已经离世。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姜唐佐远赴河南,拜见苏辙,请求完成此诗。苏辙沉吟片刻,即代胞兄苏轼为姜唐佐补足赠诗,“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苏轼眼目长”(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这是唯一一首两兄弟合写的诗。
作为苏轼的门生,姜唐佐的千里迢迢,事实上接续了恩师与苏辙尚未完结的“夜雨对床”。而颍川,则见证了一首诗的顽强生长,以及“夜雨对床”中最高音的那部分。
(作者:四川省眉山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