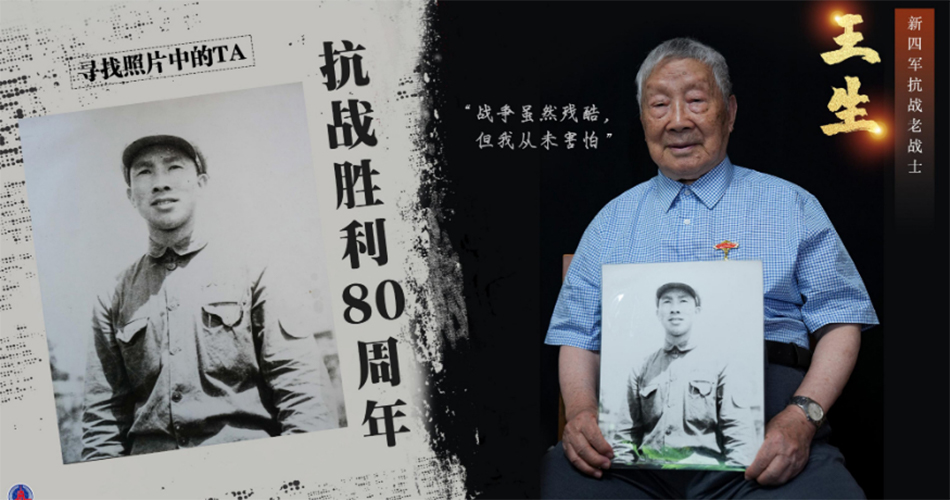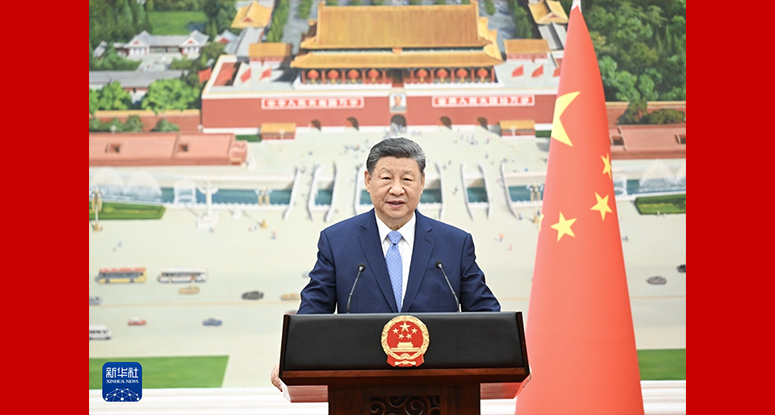濠梁最忆一钓乐
最近阅读《中国绘画史》时,书中一幅五代时期绘画大师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引起我极大兴趣。画中的远山、近水、沙滩、树木,既有节奏变化,又十分和谐,堪称一首气象万千、气韵生动的视觉“交响曲”。然而,最吸引我的是画中的一叶小舟上神态安详摇橹的老者和专注的钓虾人,这一老一少,或是爷孙,或是父子;画中还有另一钓虾者,肩负钓具,神情怡然,信步走来。我如何断定他们是钓虾,而非其他?是因为画中人手中的钓具于我并不陌生,甚至有一种亲近感,就像在他乡突然听到乡音,那般熟悉,那般亲切。
少年时,我也用过这样的垂钓工具,而且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制作过程不算复杂:取两根一尺来长、半寸来宽的竹片,相叠后在中间位置钻孔,以一铁钉或竹签为轴结成十字形,再选择一块大小适宜的方形纱布,四角与竹片四端连结做成网兜,竹片连接处再与一根长竹竿相连,一个简单而实用的钓具就做好了。当然,这只是钓虾的第一步。第二步是炒制麦麸,炒好后以香油拌匀,攥成鸡蛋大小,装进小袋里用线扎好,放于纱网中,使饵料的香味在水中可以保留较长的时间。万事俱备,钓虾去也!
去钓虾的多半是十来岁的孩子,带上弟弟妹妹或是村里的玩伴一起去。成年人是极少参与其间的。钓虾,是孩子们自发的玩乐,不像放牛羊、打猪草,是大人安排的任务。垂钓多在水面平静的青草河畔,或是荇草蔓延的池塘边。水不宜深,太深了,青虾入网容易逃之夭夭;水草也不宜盛,太茂盛,钓具容易与水草纠缠。这样的垂钓,是乡村少年独有的快乐,沉浸其间颇能忘却生活的贫困和劳作的艰辛。
钓虾的时候,孩子们常常是钓具入水后,便忘情于“抓石子”的游戏之中,任凭虾子尽情享用美味。等想到起钓时,虾们大多早已饱餐一顿,溜得无影无踪了。
钓虾之趣,颇似饮酒,尽兴为好,不可贪多。踏着落日的余晖,满载而归,固然欣喜;徜徉于田间垄上,篓中空空,又有何妨?放下钓具于水中,投入的是一种莫名的希冀;起钓时,半透明的青虾在纱网中跳跃,收获的是简单而透明的快乐。
如今想来,孩子们钓的不是虾,而是在钓一片白云、一缕清风、一杯清茶,一次心情放飞、一种乡村文化、一段年少时光。经历了生活的百转千回,早已青丝染霜;但只要回到故乡,站在青草河畔,总会忆起那群钓虾的少年,以及和畅的晚风、洒金的斜阳和淡雅的稻花香;岁月的风尘,就这样一下子荡涤而光。
其实,这样的野趣千年前就曾有过,孩子们只是在不经意地传承。看,《夏景山口待渡图》中,钓者神情怡然,老者淡定宁静,渔者踏浅浪、披斜阳,丝毫没有独钓江雪的孤寂。这样的垂钓,是寄情山水间的一种享受,是放下田间劳作的一种休闲。千年钓客,虽难道尽濠梁鱼乐,但亦非柳河东笔下的孤舟独钓人。一竿青竹,一钓千年,一千年前的钓客和今天的我们,所钓起的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道法自然、逍遥悠游之趣。快乐到底是什么?也许,这种自然的、未加修饰的、人类所共有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小时候家里有一副对联,写的是“水色山光千古秀,花香鸟语四时春”。粗细不一的笔画、浓淡干湿的墨色组合成温暖的语句,让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感到如入桃花源般的熨帖和舒畅。透过书画感悟中华文化所特有的精髓,是中国人才能体会的奇妙意境,是中华文化经久不息的重要原因。我以为,文化产品若过度包装、过多纹饰、过分虚浮,就好比十层滤镜后的人像,不仅失去原本的面貌,也容易被别人误读误解,即便暂时有“市场”,也难以在人心中留下痕迹。
(作者:安徽省蚌埠市政协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