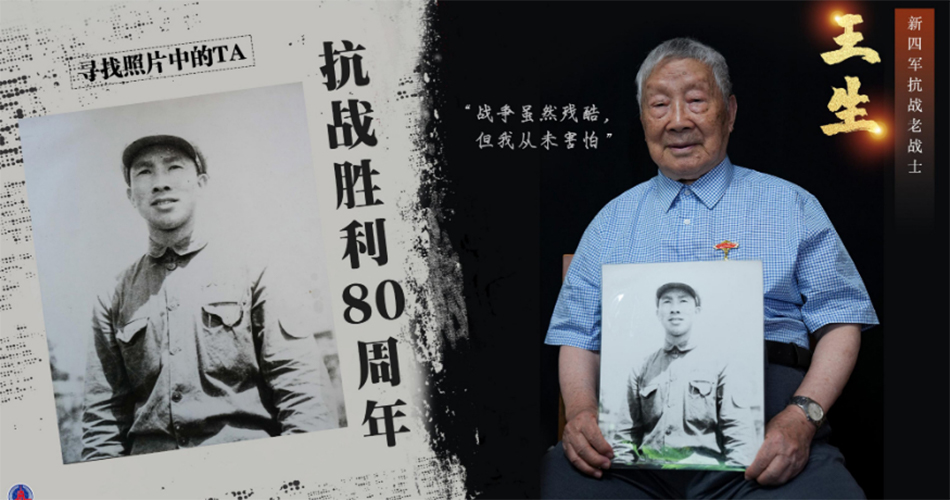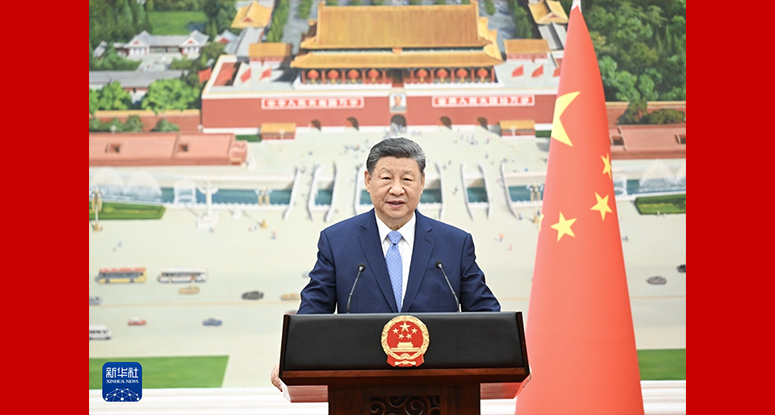打一口“深井”的执着
每个人都离不开“经史子集”的滋润和熏陶。认识历史是做学问的基础,重新发现历史则是文脉的赓续与传承。在我眼中,那些一头扎进浩繁史籍的大家,他们都是文化事业的“提灯人”,工作枯燥而严谨,编校刻苦而执着,押注生命、费心耗神去批注、删改、修订,有些时候连名字都没留下。但是,他们的史德与高标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看到做学问的态度和立场,以及打一口“深井”的毕生劳作。
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在我案头放置几个月,读的断断续续,每天掩卷思考。这本书与其说是他为多位专家补写的外传,毋宁视作中华书局的“翠微校史”——2021年末,恰逢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徐俊先生荣退,这本书是他献给“局庆”的礼物,同时也是对前辈往事、书人旧事的梳理和记录。
书名取自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点睛出作者的文心和诗情,“新书虽以‘翠微’为关键词,但实际主要涵括中华书局翠微路与王府井两个时代的书人书事……以文字重回那个时代,重回历史现场”。作者极力回望与定格的是难忘的、坎坷的、温存的学术交往细节褶皱,抑或说台下幕后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通过档案、书信、亲历、日记等翔实记载,把读者引向一个热气腾腾的历史现场。可见,“翠微”一语双关,既指向人文地理,也寓意学问之树葳蕤常青。
写书,也是写人;校书,也是做人。全书收录徐俊先生37篇文章,没有统一格式,分布不同时期,看似毫无规章,实际上内蕴着一条“草蛇灰线”,那就是关涉国史、学人、编辑的精神图谱,隔空抛给读者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学问时,该谈些什么?”有几处细节令我记忆犹新。“二十四史”点校责任编辑第一人宋云彬,在特殊时期承压点校,饱尝内心苦痛,即便这样,他也不允许出现标点错误,直到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宋云彬旧藏书画展暨捐拍仪式上,徐俊致辞时说道:“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续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徐俊的成长得益于“百年老店”中华书局的精神传统,如今他又把这个传统交付给我们,阅读与领悟的过程,本身也是向前辈们致意和学习,为文脉传承注入新的力量。
做学问要甘坐“冷板凳”。信息化时代,“冷板凳”意味着耐得住孤独、经得住考验、扛得住压力。把“冷板凳”坐热,须练得看家本领。好在,我们有榜样可寻可仿。一次署名事件里的学人风范。当年,王仲闻先生以“临时工”身份参与《全宋词》修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重印七次六万册的《全宋词》却没有他的名字。直到1999年《全宋词》简体本出版,才修订补上,载入史册的不仅是姓名,更多的是他的情怀。一个编校的温暖故事。何兹全先生是中华书局的良师益友,95岁那年参加“二十四史“专家论证会时说道,“对中华的修订工作,我很高兴、很赞成,愿意做一个小卒,摇旗呐喊。”而傅璇琮先生身处艰难环境,做出超出同辈的学术贡献,他却在自选集序言中袒露心声:“最大的心愿是为学界办实事,最大的快慰是得到学界的‘信知’。”他是自勉,也是出于一份情怀。
昔日学人的风范,吉光片羽也闪烁着人格光辉,蔡美彪负责主编范文澜《中国通史》,自己的著作一直未能再版,他却强调,“只要还能写,就不去编。”后来他的著作出版,他说道,“我出这两本书,都是几十年前写的,对我来说是‘清仓甩卖’,对中华书局来说是‘废品回收’。”一位幽默、谦逊、可爱的老先生呼之欲出,令我心生敬仰。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佳话,总是令人津津乐道。因出版《管锥编》《谈艺录》,周振甫与钱锺书交往甚密,徐俊整理出的“审稿意见”从中可见一斑。周振甫请他酌情修改:“‘请益’、‘大鸣’、‘实归’是否有些夸饰,可否酌改?”钱锺书在行侧批注:“如蒲牢之鲸坚,禅人所谓‘震耳作三日聋’者,不可改也。”有源有据,不亢不卑,令人为之动容。这段经历也被写进《管锥编》序言中:“命笔之时,数请益处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小叩”与“大鸣”,犹如心灵弦乐,悦耳动人,而“一生作嫁,却安之若素,甘之如饴”的学术风范,也会走向不朽。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学者刘再复为什么会说,面对钱锺书这一大海,做学问苦海无边,意为抵达钱锺书先生的彼岸难以企及。
每篇文章都是一个人的断代史,当轮到写自己时,徐俊先生内敛而低调。他以《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为题,分享亲历、亲见、亲闻编往故事。从1979年考入大学到进入书局工作,四十年的光阴,留下太多难忘的瞬间。从一个不会捆书的职场“小白”到千锤百炼的扛大旗者,徐俊深得老编辑们的教诲和示范,“不管你进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最后都被塑造成中华书局人的那个样子。”这种影响“润物细无声”,他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功夫到家了,就会水到渠成。当然,数十年如一日去打一口“深井”,需要精益求精。正如周勋初先生的观点,“研究哪一个学科,真正要弄到最高端,一定要靠精品,太烂的东西还是少沾,沾手以后,把自己的品牌搞坏掉了。含金量的东西还是重要的。”专精绝学、求精臻善、学有所守、宁恨毋悔,乃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鉴照,何尝不是为现代人求知尚学留下的一剂“清凉贴”呢?
打一口“深井”的执着,诚实、善思、坚毅,一个也不能少。我出生和成长在高校家属大院,后来成为青年作家和文化界别的政协委员,多年以来的孜孜求索告诉我,文化事业是“慢活儿”,笨拙地写比较快,勤恳地钻才有收获,坚持地做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徐俊的“翠微校史”使我更加坚定脚下的道路,认识到赓续文脉需要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不忘来时路,走好眼前路。书的封面照片为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定格学林往事的精神光影,在我的心灵投射下一束光芒,永远引领笃毅前行。
(作者:山东省济南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