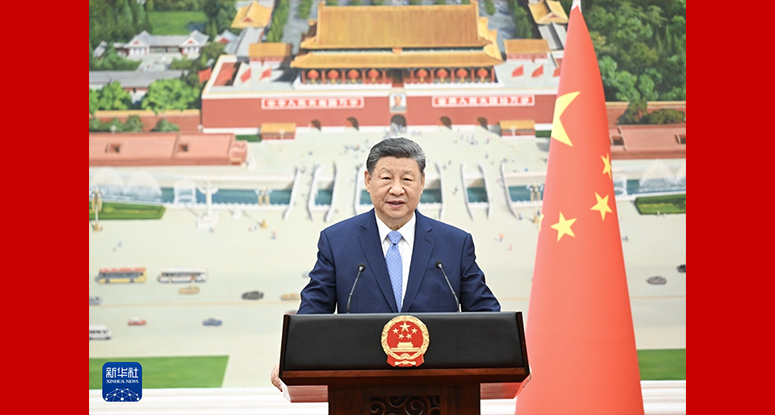仰望星空,思接宇宙——读杜甫《登高》
杜甫是在大历元年暮春抵达夔州的。或许是严武突然去世对他打击太大的缘故,杜甫离开成都不久身体就状况不断,不得不在云安居留休养,他在致岑参的诗中说,“泊船秋夜经春草,伏枕青枫限玉除”,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向这位老友报告了自己的病况。到夔州后,杜甫再次居住下来休养,整个夏季,他都在与疾病作斗争,“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
此时杜甫的身份还颇为尊贵,曾经的左拾遗、剑南节度判官,现在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这种身份使他不太可能受到轻慢。初到夔州,官府把他安排在西阁居住,他一边休养,一边整理自己的诗稿。西阁是政府招待所,其位置在白帝山西侧半山腰,背靠绝壁,下临长江,站在阁上,可以看到自西边蜿蜒而来、明亮而呈黄褐色的长江。
《登高》一诗就是在这年(766年)的秋天写成的,很有可能就写于西阁。理由是,杜甫在夔州的几处居所中,只有西阁在黄昏时分才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观。长江滚滚“来”而不是“去”,表明杜甫此时正向西面对那条激情四射、自由奔放的巨龙。
这首诗被归于悲秋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所开创的这一诗歌主题对杜甫影响至深,他说过“清秋宋玉悲”这样的话,在《登高》一诗中,“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就化用了宋玉的“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在中华诗歌的传统中,悲秋具有反身性,“悲秋”与“悲己”是同一件事。
这首诗前三联气势恢宏,深邃广大,尤其是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堪称秋之交响,被历代诗论家视作“旷代之作”,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写尽了身世之悲,后世多少游子反复吟诵,视老杜为知己。
然而,尾联却没有延续此前的波澜,而是突然转向了,“潦倒新停浊酒杯”,戛然而止,就像一部史诗级大片,剧终时舞台上只剩下一只空酒杯,与观众的期待反差太大了。结尾显得有些软,有点冷,似乎接不住前面酝酿起来的悲秋情绪。
可以设想一下:宇宙无限苍茫,落叶纷纷,江水滔滔,猿声哀鸣,百鸟回巢,我们的诗人拖着病躯,登台遥望,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我们的诗人该拿什么应接这无边的悲伤呢?极致对应极致。对应这无边悲伤的恐怕就只能是死亡了吧?
宋玉就是这样面对秋天的,在本文前面引用的他那段诗句之后,宋玉提到了死亡:
岁忽忽而遒尽兮,恐余寿之弗将。
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
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
心怵惕而震荡兮,何所忧之多方!
宋玉“悲秋”情绪的演变是符合“逻辑”的,反身性要求结构的均衡,这是“清秋宋玉悲”成为名篇的原因。可是,杜甫没有这样写,在读到“艰难苦恨繁霜鬓”之后,读者期待的更悲伤的情绪没有出现,代替它的,是一个戏谑的、调侃的表情包。诗人以一句自嘲回应了那种压迫感极强的宇宙力量。面对无限的宇宙,此老只是捻须一笑,呵呵,喝不了啦!
这首诗呈现了伟大的宇宙与渺小的个体之间不对称的张力。在苍茫的宇宙中,人类个体犹如飘飞的秋叶,杜甫对人类的这一处境不仅有洞察,而且自己就体验着这种处境。但是,杜甫用一只空的酒杯便化解了这一处境。
需要纠正对杜甫的刻板印象,好像他总是“哭哭啼啼”,不停地抱怨自己志不得展,渴望回到皇帝身边。杜甫不是这样的人,他有着幽默、旷达的天性。不错,他是写尽了人间悲苦,但在夔州,他获得了在宇宙的尺度上看待人类命运的新认知。道,具有无限的吸纳性,小可以容纳大,弱能够支撑强。道性赋予杜诗以魅力,他总能举重若轻,他从不叽叽喳喳,板起脸讲大道理。杜甫是一个得道的诗人。
杜甫在夔州的时间并不长,前后25个月,却创作了近500首诗,差不多占其存世诗的三分之一。夔州诗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考虑到他糟糕的身体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我的看法是,这一奇迹要用他居于夔州时对宇宙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带来的对天道的新认知来解释。他每天晚上都仰望星空,观察月亮、星星,倾听宇宙的声音,这一时期的诗里一再提到这一点,如“中夜江山静,危楼望北辰”(《中夜》),“江喧长少睡,楼迥独移时”(《垂白》),他把这些观察记录下来,写成诗。“日日江楼坐翠微”“中宵步绮疏”,杜甫为自己画了一幅像,一个思考者,一个仰望者。对宇宙的新体察,重塑了杜甫的生命观和历史观。
《登高》体现着杜甫在夔州获得的认知上的突破,类似的诗篇还有《秋兴八首》《诸将》《八哀诗》以及一系列回忆往事的诗,把这些诗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就能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风格,沉静、深邃,如哲人一样的思考。这一时期的诗多长篇巨制,其中一首长达百韵,200句,思如江水,滚滚而来。夔州之思、之诗,标志着新杜甫的诞生,一个立足于宇宙秩序思考个体和王朝命运的杜甫。
(作者:中国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