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园的风景与风云——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
【读书者说】
对于现今的国人而言,大概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会有一座公园——或是阖家欢乐的流连之所,或是同学少年的游戏之地,再或是情窦初开时的徘徊所在,你我的成长历程大都有公园相伴。而今,无论大小城市,公园更是成为居民生活半径的“标配”。但这道日常的风景,其实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仅有一百多年的时光。和衣食住行等更为恒常的生活方式相比,中国人之“逛公园”尚属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体验。
青年学者林峥新近出版的《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以下简称《公园北京》)即系统考察了“公园”这一舶来品自晚清始入华土,至抗战爆发以前充分“中国化”的过程。在作者看来,“公园是现代都市之心,对于公园的构想,体现了对于城市的理解和想象”。海德公园之于伦敦,中央公园之于纽约,便是如此。建立在现代城市理念基础之上的公园观念,实为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对于“人与城市”“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一系列关系探索的产物。因此,内在于“西学东渐”进程中的“西园东渐”,首先是全球现代性扩张的一种表征及其在东方坐标上的显影。但《公园北京》的抱负却远不止于勾勒出这一新兴的物质空间与价值体系自西向东的全球旅程。与世界眼光相比,作者更为在意的是探究“公园”在风云变幻的现代中国是怎样实现在地化、本土化,亦即“中国化”的。用她的话说,便是经由追踪中国公园的前世今生,辨析“一种更切合中国自身语境的现代性”如何可能(第28页)。这一问题意识突出体现在“公园北京”视野的建构与展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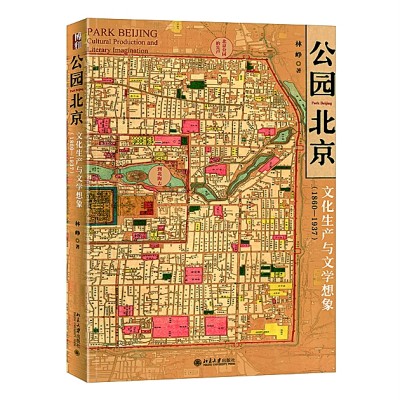
《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 林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资料图片
公园北京 现代中国缩影之一种
作为“首善之区”,又是公园“舶来”时的首都,北京成为《公园北京》的研究对象似乎无需多言。但其实不然,尽管中国的园林传统源远流长,却是“类皆个人独乐,例不公开”(陈植《都市与公园论》)的私家花园,与以公共、公用、共享为取向的公园具有本质区别。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在中国率先出现在1860年代的上海租界,若论中国公园史,是应该从上海说起的,但租界这一半殖民地空间的特殊性质,却使得其时建造的公园无论建设理念、服务对象还是实际效用都几乎非但与本土无涉,还更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社会的隔阂。直到1907年,清廷在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之上建成面向全体市民的万牲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公园在中国才真正开始本土化。而万牲园作为中国本土公园的起点,其隐喻意义还包括“在北京公园诞生之初,即奠定了一个思路,不是另起炉灶新建西式公园,而是充分利用帝都丰富的名胜古迹”。这也就昭示了与横向移植西方经验的上海公园不同,北京公园从一开始选择的便是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之间融合、转化与再造的道路。这显然不仅是一条公园之路,也关乎对于“另一种现代性”的尝试。是故林峥才说,“北京是中国的缩影,而公园则是北京的缩影”。(第28页)
公园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缩影之一种,原因在于其和现代中国同构共生。万牲园开张于晚清新政的时代氛围中,而伴随着民国肇立,北京更多公园的开放也提上日程。1917年,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呈文《请开京畿名胜》获批。同年,社稷坛作为由“京畿名胜”转化而来的首家公园对外开放,此即中央公园(现今中山公园)。尔后,先农坛、天坛、太庙、地坛、北海、颐和园、景山与中南海等也在1915年至1929年间相继开放。北京一时成为一座公园的城市。而公园建设除去推动城市发展,更为重要的功能还有教化公民,培育共和社会的基础。公园之“公”与共和之“共”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林峥发现,“近代中国的启蒙价值观与西方公园的教化功能不谋而合”,“迫切养成不同于‘东亚病夫’的、文明健康的现代国民”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公园的教育(包括美育、德育、智育、体育)功能被进一步凸显”。(第13页)因此在北京各家公园中,一方面是图书馆、讲演厅、博物馆、音乐堂、茶座、餐厅与各种体育设备的到位,另一方面则是教导公民得体使用公共空间的规章制度的出台。“这些有形和无形的符码,不仅旨在规范一个有序的公共空间,更是从身体上、理念上规训‘文明’的现代人。”(第14页)而这正是公园作为一种现代公共空间的题中之义。
当然,这只是北京公园登上历史舞台的大背景与主航向。各家公园在鼎革之际由原有宫苑转身出场,其来龙与去脉要丰富与复杂得多。不管“北京”还是“公园”,都并非铁板一块。北京公园日益落地与立体的过程,也是其分化与多元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融合了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与社会力量的博弈,也见证了不同阶层的生成、流动、碰撞与各得其所。《公园北京》书分五章,分别讲述了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与陶然亭的故事,“恰好一一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新青年、普通市民、政治团体这五种人群的生活及表现,同时也分别反映了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功能”。(第18页)由是自然可见作者的匠心与巧思,从“公园北京”生发的如许面向能够铺得开并且拢得住,还是说明了,在深耕厚植的本土传统与波云诡谲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出来的北京公园自有非比寻常的风景与风云。
“园中之人”的精神气象
想要道出北京城市空间的故事并不容易。如何将建筑史、城市史与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熔铸一炉并且彼此发见,这是《公园北京》必须面对的挑战。作者为此设计的策略是构建了“公园”的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物质景观,二是作为文化实践空间,三是作为被表现(以文学为主)的对象。书中的五个个案都是从物质层面切入,但更为关注的是“园中之人”——公园的设计者、使用者与书写者。于是,万牲园中的梁启超,中央公园里的胡适、鲁迅与京派同人,北海公园中的沈从文与一众文学“新青年”,城南游艺园里的张恨水,陶然亭下的少年中国学会与毛泽东、高君宇、石评梅……半部现代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人物都在北京公园中轮番登场。以“园中之人”为主体,也以“园中之人”为中介,公园风景的背后涌动着时代风云。从《公园北京》可以总结出,北京公园与现代中国的内生性关联体现为“符码”“历史”“彰显”与“精神”四个方面。
首先是作为一种现代“符码”。“来今雨轩的过客——京派文学的公共领域与生产机制”一章详尽考辨了中央公园何以在1920年代成为“新文学”作家聚集的胜地,进而到了1930年代跻身于“太太的客厅”(林徽因主事)、“读诗会”(朱光潜主持)互通声气的京派文学生产空间。这一“地上的公园”与京派“纸上的公园”——《大公报》文学副刊(该刊甚至一度就叫《小公园》!)密切互动,以“聚餐会”联络同人,又以“茶会”培养新军,共同促成了抗战爆发以前京派的繁荣。空间的“符码”由此成为文学的“符码”。
其次,北京公园本身还是一种“历史”。“陶然亭风景的流变——招魂、革命与恋爱”一章即介绍了从遗老群体到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再到“小团体,大联合”的革命志士在陶然亭这一空间嬗变的过程。这不啻为现代中国的缩影。公园的景观性与政治性在此相互成就。作为新中国在北京建立的首家公园,陶然亭的故事原来在1920年代便“伏脉千里”。“到北海去——新青年的美育乌托邦”一章则提示了“公园”作为“历史”的另外一种向度。同样是北海公园,它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心仪的“现代美育空间”,是“新青年”造梦的“文学乌托邦”,但也是园外批判小资情调的主要对象。待到北平沦陷,北海公园又成为民族创痛的记忆,承载了欲说还休的创伤。1955年,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大江南北,少先队员在北海泛舟的形象凝聚了整个国家的希望。“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阶级立场和相应的美学观下,对于北海的看法会发生变化。”(第178页)“看法”也是“历史”,其中寄托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情感、追求与想象。
“公园”更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彰显”。“北京公园的先声——新旧过渡时代的士大夫与万牲园”一章追索“北京公园的先声”万牲园的兴建过程,发现其“中西合璧、新旧并存”的特征正是“民国北京公园最大的特色”。(第91页)而所谓“合璧、并存”,意味着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叠印其间。在“公园北京”的视野中观照现代中国,万牲园无疑是最佳入口,也是最好写照。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绝非简单的“调和”,而是伴随着万牲园开园以及士大夫与市民阶层的广泛参与,“传统”最终还是被带入了“现代”,并且成为“现代”的组成部分。在公园这一空间界面上展开的现代中国的隐喻,迄今未已。而除去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北京公园彰显的还有光明与阴暗的纠葛。“游艺园、社会新闻与通俗小说——城南市民消费文化”一章揭示了曾经与中央公园、北海公园三足鼎立的城南游艺园何以走向衰落,提醒我们公园也有可能会被异化,对于“现代”的理解中也应当包括对其背面乃至对立面的警觉。
最后,“公园”是一种“精神”。为什么需要公园?在《公园北京》中可以找到国家、社会、知识分子与市民的各种回答。正是各方的合力,汇成了北京公园的横空出世,继而大放异彩。但除了这些,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答案?林峥讲述的萧乾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期间编者、作者与读者互动的故事,或许不无启示。萧乾强调,副刊乃是一种“圆桌”:“一张圆桌,不是课堂,也永不可成为沙场。”(萧乾《读者与编者》)这是早在沈从文主编时期就树立的风气。王西彦回忆,沈从文喜欢召集青年作者到中山公园进行“漫谈式的聚会”,“他只是一位年龄稍长的大朋友,他也从不摆出一副导师或主编的架式”。(王西彦《宽厚的人,并非寂寞的作家——关于沈从文的为人和作品》)而从沈从文到萧乾,这一“漫谈式的聚会”也从“地上的公园”移到“纸上的公园”,其中充盈的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共同创造的精神,也成了京派的核心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正是“公园北京”最为重要的精神。
林峥注意到,“长期浸淫于北京文化、曾是中央公园常客的知识分子,由京迁沪后,却极少光顾上海的公园”。(第109页)胡适与鲁迅在1920年代的北京公园都留下诸多足迹,但在1930年代的上海却不再涉足公园。萧红就记得,鲁迅“住在上海十年”,“不游公园”。(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这是饶有意味的发现。除去不同的城市性格、公园氛围,不同的“园中之人”具有的精神气象,以及时过境迁的心情是否才是胡适与鲁迅作别公园的更为深层的原因?风景的背后是风云,精神流散的公园也许就不再是“公园”。
为什么谈论公园时会不由自主想到“风景”与“风云”这些词汇?这和二者指涉了公园的物质性、情感性与政治性有关。但与学理剖析相比,这恐怕更多源自生活体验。两者都与“风”相关。而“风”正是一种“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龚自珍《释风》)的存在。作为现代城市空间的公园,固然有其现实规定性;可借助文学、图像、声音、记忆,当我们置身其中时,想象力却得以自由驰骋。在规定性与想象力之间,便是公园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搭建起的一座心灵的桥梁。我们需要公园,乃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方“文明”“教养”与“自由”兼具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天地。
(作者:李浴洋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