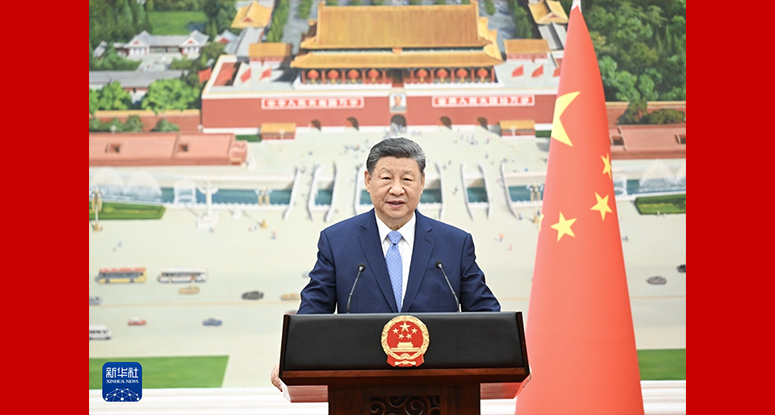阅读:在拓展的背后
作者:彭程(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读书无止境,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中,书与书之间时常构成某种关联,它们跨越时空相互映照、呼应。寻找到这种关联,阅读的边界就会不断拓展,阅读者就会努力敞开胸怀拥抱广阔,拥抱世界。
壹
一个醉心阅读的人,随着目光的不断扩展,他心中将会浮出这样的发问:他读过的成百上千本图书之间,有没有建构起来某种关系?是楚云燕雨,相互隔绝遥遥无缘,还是吴山越水,彼此呼应地脉相连?
不论开始时情形如何,这早晚会是他将遇到的问题。在某个时辰也许他会发现,伴随着这种发问,某一个可能的答案,会以一种诉诸画面的形象的方式,在他的想象中缓缓浮现和展开。
这幅画面可能是一幅山水风景,他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画面上的一个细节,一道笔画,一处局部。哪一本犹如岩石兀立,哪一本好像修竹摇曳,哪一本看似出岫之云,哪一本仿佛高翔之鸟?
它也可能让人想到一张刚刚被拉出水面的渔网,在阳光下水珠闪闪发亮。众多丝线和辅料,被编织连缀为一体,以完成捕获鱼类的任务。在诸多彼此勾连交织的线绳中,谁来作为着手编织时的网纲?谁来充当连缀众多网片的一个个绳结?谁又是卡住落网之鱼胸鳍的网囊?那一串串沉重的铅坠又是如何封入?阅读的行为,有时也会让人想到仿佛是在编织一张渔网,每一本书都作为零部件被嵌入相应的位置。
如果将想象的尺幅放大一些,那么你可能面对一片广袤的田野,阡陌交错,原隰相连。田埂区分开不同的作物区域,而一排排树木连同其所掩映的道路,则成为相邻村庄的分界。这样的每一条路径,是在阻隔中完成了连接。阅读中不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你以为脚步是在某一个知识领域,却不觉迈入了另外的领地。
这并非出现在阅读者眼前的真实空间,但对于一个得其三昧者,在他的心中,那种连通却是真切的。就像暗物质、三维空间、量子纠缠等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及其结构和运动一样,平时难以感知,但却是确凿存在的。
如果他不满足于仅仅从远处观赏这一幅幅场景,而是走入其间,行走端详,他会有源源不断的发现,会认识到这些画面中诸种元素之间的勾连、纠结和缠绕,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关系的范畴之内。它们别有洞天,丰富多彩,真实而又玄妙。
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有一个颇为突出的现象。一位作家诗人,因为气质禀赋相近,或身世遭遇类似,对前代的某一位同行格外倾慕,倍感投契,将其尊奉为心目中的良师益友。仿佛一只野兽,能够隔着茂密的树丛嗅到同类发出的气味。
陶渊明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于今无人不晓,但在他生活的晋宋时代,以及身后数百年里,却是寂寂无名。尽管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其所编《文选》序言中对他大加褒扬,唐代李白、孟浩然、白居易等诗人也都表达过仰慕之情,但总体上并不广为人知。一直到了北宋,因为苏东坡无以复加的推崇,他的价值才获得了深入的认识,真正确立了文学史上的地位。苏东坡乐观豁达的天性,对于平淡冲和生活的向往,让他格外喜爱洒脱淡泊、委运任化的陶渊明,准确地把握了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风格特质,并写下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苏东坡堪称当时的超级文化宗师,他的喜好自然会影响到民众的欣赏趣味。
“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在自己的诗篇中,多次提到两百年前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庾信,这两句诗更是被后人广泛引用。北魏降将侯景的叛乱,导致梁朝覆灭,江南繁华尽毁于连年兵燹。作为梁朝使者的庾信,被迫长期滞留北朝的西魏和北周,无法回到故乡。社稷倾覆,身世蹭蹬,儿女夭亡,血泪交织的沉痛感慨,在其晚年的名篇《哀江南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杜甫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时代,遽然遭逢安史之乱,陵谷变迁,流离失所,与庾信的遭遇格外相似。这位充任了时代的书记官角色,写出了“三吏”“三别”等泣血诗篇的悲愁诗人,时刻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为百姓的苦难哀悯,见花开而溅泪,闻鸟啼而惊心,因此很自然地会对庾信其人其作产生共鸣,可谓异代而同慨。
作为后来者,他们倾慕仿效的文字仿佛一道道火烛,照亮了幽暗中的一条通道,显现了昏昧时光中彼此之间的感应和映照。这是一个长时段的故事,缓慢地展开在千百年浩漫的时光中,你仿佛看到一个伫立在田野中向着远方拜谒的人,身影被日光投射在地面上,拉得很长。因此,对于一位阅读者来说,这些前人仿佛是一个个路标,矗立在他的阅读之路的旁侧,指示他迈步的方向。
这样一种穿越岁月的联系,有时呈现为一种群体行为,时代精神的激荡,成为背后最强有力的推手。以韩愈、欧阳修为旗手的唐宋古文运动,力求摆脱六朝骈俪文章的浮华靡弱,向先秦两汉散文的朴质厚重汲取营养。几百年后的明代中期,类似的一幕再次搬演,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抨击的目标则是当时流行的内容贫乏、形式雍容的台阁体文风。虽然这一思潮主要体现为诗歌的变革,其成就和影响也无法比肩前者,但就其本质而言,却同样是一次名为复古而旨在创新的对于时弊的反拨。
沿着这种路径而展开的阅读,其实质是一种寻找和呼唤,仿佛鸟翔于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从某个立脚之处,他望向四方,寻找视野中的相关风景,在心中为它们归类。而随着不停地迈步行进,他会拥有众多的站立处,也因此会不断地扩大和累积眼中所见。
对于一位真正的阅读者,这种行为在时间中的展开,是视野的步步扩展,书籍的不断积累。这一种状态可以伴随他很长时间,也许是终身。在某个时候,他会惊叹于自己丰富的拥有。那一份坐拥书城的感觉,不亚于南面而王。
这种现象,会让人想到南方山野里经常见到的风景,一棵榕树陆续地滋生出新的气根,向周围延伸,几十上百年后,原来的独木已经繁衍成为一片树林。
叁
金克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书读完了》。他提到一则轶事,大学者陈寅恪年轻时曾拜访一位历史学家,老先生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估计很多读者乍一看到这个说法,会感到不可思议。中国古籍图书浩如烟海,谁敢说自己能够穷尽?这个说法不啻一个挑战,一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但一个对阅读饶有心得的人,大概率会像金克木先生一样会心一笑。他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论。这种反应,来自他在阅读实践中获得的对于书籍之间关系的认识。
书籍固然数量浩如烟海,但其轻重分量不同,不可等量齐观。大量的书实际上可有可无,不读也没有明显的损失。只有极少数才真正具有原创意义,是那种被称为经典的书籍,是书中之书。作者是这样说的:“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
金克木先生列出了一个符合这种标准的书籍:《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庄子》《道德经》《史记》《资治通鉴》《文选》……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域外: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这些大思想家、大作家的著作,作为不同文化的根源和基础,都具有元典的意义。
这一类的书籍,在每一种文化中,也不过几十种。围绕着这些书,又会产生很多注解和阐释,然后是注解之注解、阐释之阐释。后者都是依附之书,数量成倍地增加,仿佛水面上一圈圈扩散的涟漪。这种现象,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构成了一种“古书间的关系”。那么,对老学者的“书读完了”,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显然他们是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这个密码本在手,可以有效地辨识出彼此间是否属于同一阵营。
在同一篇文章中,金克木先生还写道:“这些书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质量极高,又像堡垒,很难攻进去。”但如果想进入一种文化精神的内部,洞悉其基本结构和质地,就别无选择,只能迎难而上。
试着运用这种眼光,就会获得新的发现或者理解。像儒家思想,无疑是绵亘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广阔原野上的一条主干道。早在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人为这条大路立下了奠基开辟之功,汉代董仲舒则推动了心性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变,大幅度地拓宽了路面。到了宋明时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给予了创造性的发展,弥补了传统儒学在本体论和思辨性方面的不足,构建了更为精致和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仿佛在将一条年久失修的老路重新加固时,采用了新的技术和材质。一条通和变、继承和创新的清晰可见的线索,贯通于两千年的漫漫时空中。
这些经典所阐扬的精神,又寄寓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门类的书籍中,以不同方式得到播扬。诗言志,心声的发抒化为诗词歌赋。就行仁道、安斯民、固社稷这一儒家精神的核心内容而言,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正气歌》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这种理念激发出的情感表达。它们在历代人的口中不停地吟诵,成为一种集体的潜意识,作用于世道人心,潜移默化地实现着人格的铸造。
因此,如果将这一个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系统,比拟为一个广阔的园林,那么四书和五经是参天大树,众多的集解注疏仿佛其下茂盛的灌木丛,至于那些开蒙家训等读物,则不妨看作林下的一丛丛野草杂花,而卷帙浩繁的诗词文赋,不是可以想象为一阵掠过林间的风,挟带着松脂的香气和叶片的簌簌声?
从这些不同的作品和书籍中,我们看到了母体和子嗣,源头和水流,树干和枝叶,枢纽和节点,核心和外围,懂得了纲举而目张,看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了解了种种繁复纷纭的逻辑关系。“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文学的本末源流的探讨,正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联系的特点、方式与途径的写照。
我们恐怕永远没有资格说出“书读完了”这样的话,但却可以借助这个说法里透露出的那种思路,对所读和将读的书籍进行辨识和甄别、筛选和归类,让彼此之间脉络宛然,眉目清晰。
肆
很多时候,书籍之间的联系是天然的,是一种先期的预设,是阅读者不假外求就可以获致的认识。从根本上讲,它起源于事物本身的多维属性,来自世界构成的混同状态。
最常见也是最直观的联系,往往体现于同一本书的内部。这样的一本书会显示出不同的面相,就仿佛东南亚国家的四面佛雕像,向着四方投送出慈悲的微笑,又像是一栋公司大厦里众多外观完全相同的房间,其实承担了不同的科室功能。尤其在知识尚未被细致分工的时代,这种情况十分普遍。许多书籍就其文体形式而言,没有泾渭分明的清晰界定,非此即彼,而是经常体现为一种交错融合状态,亦此亦彼。譬如在中国古籍中,《左传》和《史记》是历史著作的典范,《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是地理志书的楷模,但同时它们也是文学作品,是古典散文的巅峰,是一代代后人追摹的范本。更不必说《庄子》的汗漫恣肆,《老子》的言简意赅,各自折射出一种极致状态的美学风貌。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就是对此现象的一种通俗的表达,而其实质正是知识形态的相互渗透,难分轩轾。
面对这样的情况,与其说阅读者要建立不同知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不如说是要努力发现这种联系。就像一个人走进莽莽苍苍的原始密林,看到一棵苔藓遍布的粗壮大树上,缠绕蒙络了不同的藤蔓,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分辨出植物分类学意义上它们各自的科属。
文学作为对生活的复杂而生动的提炼整合,这一特点表达得最为明晰。陆游把恢复被金人占据的中原作为毕生志向,用情之深,执念之重,世罕其匹,浮现在深夜的梦境里,也发抒于绝笔之作中。“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夙愿难酬的沉痛,被发抒得淋漓沉痛。吟诵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仿佛望见一个孤独英雄伫立秋风的悲凉身影:“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位开创一代词风的大家,更是一位既有勇气又富韬略的将帅之才,但皇室苟且偷安于残山剩水,不以光复为念。他壮志难酬,被迫赋闲数十年,“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愁闷只能向山水间排遣。即便是仅仅为了深入理解上述诗句,也需要了解这一段先之以宋辽对峙、继之以宋金仇怨的历史,了解杨家将的民间传说,徽钦二帝屈辱的“北狩”,岳飞《满江红》中的壮怀激烈。这是发生于阅读中的一种自然的催迫,驱使你的目光穿梭于诸多领域,就像脚步跨越广阔原野间的一道道田埂。
也有另外一种缩敛退隐的人生,向着大自然的深处,草木茂盛的桑间陌上,云霭缭绕的山中泽畔,缓缓迈开步履,归去来兮。欲熟谙陶渊明,怎么能不去了解一番庄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让人想到庄周在妻子去世时的鼓盆而歌。想读透王维,如何能够对佛教一无所知?“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澄怀静虑,风神萧散,仿佛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朴素平淡或清新明丽的诗句后面,关联了不同的智慧资源。
一种书籍的内部是这样,那么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书籍之间,最为常见的情形,是彼此都受着相同的时代精神的浸润。仿佛盛夏季节的一阵豪雨,落在树丛间,落在江河里,落在田垄中,湿润的气息更是弥漫于天地之间。
东汉末年,皇室衰微,军阀混战,白骨蔽野,民不聊生。以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发出了匡扶社稷、救民于水火的呐喊。“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的这番豪气干云的话,表达的也是集体的心声,发为诗文,便形成了悲凉慷慨、极具感染力的整体风格,被后世誉为“建安风骨”。到了唐代初年,在新兴王朝开放昂扬的时代氛围中,以王勃、陈子昂等“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年轻诗人,满怀建功立业的豪情,为诗歌注入了刚劲豪放的精神,其睥睨古今的倜傥意气,也让人想到建安风骨的梗概多气。二者都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产物。博尔赫斯曾经反复表达过一个观点,“历史总是不断地再现”,这两个前后相隔四百多年的作家群体,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文学角度的佐证。
总之,只要开始了阅读,一种机制便自动开启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与阅读者的心驰神骛相同步,一些想象中的樊篱被撤除,屏障不复存在。一种范畴会自动延伸,与另一种范畴连接,一个时代的声音,在另一个时代发出回响。它们会主动地寻找和辨识,呼朋唤友,连类比物,声气相投,惺惺相惜。
精神的产生和发育,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迹可循。生态文学在今天的美国已经蔚为大观,其理论渊源是哲学家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所表达的超验主义思想,其挚友梭罗又在散文名著《瓦尔登湖》中,给予了形象化的阐释,强调了大自然对个人成长的启发。一百年后,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利奥波德,在代表作《沙乡年鉴》中强调自然环境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将人的姿态放低,认为人类作为土地共同体的一员并没有特殊的权利,任何僭越的行为都是对大自然和谐状态的戕害。接下来又是蕾切尔·卡森,她的划时代的《寂静的春天》,直面技术畸形发展导致的生态污染恶果,大声疾呼停止饮鸩止渴的行为。近两百年间,以这三部被誉为“美国自然文学三部曲”的作品为代表,几代作家用数量可观的作品,丰富并提升了这一后起的文学流派,使得这一文学新树种不断地开枝散叶,茁壮生长,成为文学园林中一角美丽别致的风景。
伍
如果说在上面的情形中,联系体现在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的内部,随着时光的延伸而生长繁育,是一种时间维度中的存在,那么它同样也具备跨越地域的属性,构成空间维度上的映照与呼应。
基于人性的相通,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相同远远大过相异,共性明显多于个性。这一点也成为彼此间产生关联的一条情感纽带,为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奠立了基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朴素的说法,正可以作为统摄这种相通性的总纲。一根琴弦,埋设在不同的文字之间,等待被心灵的手指弹拨,琮琤作响。
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曾经受到中国文化长久而深刻的哺育,因此读《方丈记》《徒然草》等日本古典随笔时,每每感受到一种颇为熟悉的情味。白雪消融、残月在天、樱花凋零,都能唤起作者们内心的怜惜和哀愁,大自然景物的变迁,让他们感悟生老病死、诸行无常。一种被称为“物哀”的美学意识,弥漫在众多篇页之间。这些岂不令人想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反复吟咏的主题?就像那首《驱车上东门》中所咏叹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如果说后者更为沉痛凄怆,该是与彼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天下板荡,世积乱离,命如草芥,朝不虑夕,让思索变得更加深切和尖锐。
生死事大,死亡永远是一个凝重的话题。还是同样的喟叹,这次目光自中土开始,向着西方挪移。西晋时代的豪富兼文人石崇,在其洛阳金谷园别墅举办“金谷之会”,邀召著名文士宴饮歌咏,兴尽悲来之时,各自赋诗并结为一集。石崇在为其所作的《金谷诗序》中,揭示了这些作品背后的核心情感:“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几十年之后的东晋永和年间,另一场远比它更为出名的文人雅集,在浙东会稽山下的兰亭举行,作品亦汇集成册,王羲之为之作《兰亭集序》,表达了类似的怅惘感慨:“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自华夏一路迢遥向西,走入群山环绕的伊朗高原,古代波斯的诗人奥玛尔·海亚姆,在《鲁拜集》中的一百多首四行诗中,感慨人生如寄、盛衰无常。“天地是飘摇的逆旅,昼夜是逆旅的门户;多少苏丹与荣华,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郭沫若的译文,流溢着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这样的关注应该是必要的:如何发现辨识其间的同与异,它们分别来自所属文化中的哪一种规定性?
另一方面,有焦虑忧惧,同样也有豁达从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先秦时代庄子的旷放达观。一千多年后,北宋理学家张载则有这样的说法:“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顺生安命的姿态,是时间之流中的延续,也是儒道学派的共识,可谓是中国智慧达成的一个公约数。万里之外地中海旁的古代希腊,一个被称为斯多葛主义的哲学学派的生死观,也会让人嗅到同样的气味。这一学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其《沉思录》中表达了对生命必将走向消亡的镇定泰然:“请自然地通过这一小段时间,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
上面都是属于生命与生活的根本层面的问题,当涉及某些专门领域和具体话题时,这种连通就更是毫无阻隔。像前述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主流思想的生态保护意识,在东方这一片信奉“天人合一”的广袤土地上,也正在被如火如荼地传播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便是一种形象化的表述。当然,它能够获得呼应,首先因为它的许多理念原本也属于本土固有的精神资源,如《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涉及这一内容:“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当代众多秉持这一理念的写作者,也正在热情地描绘属于中国自己的生态自然文学景观。
如果能够梳理出这样的脉络,阅读就不会故步自封,就没有藩篱边界,就会努力敞开胸怀拥抱广阔。某一颗灵魂发出的信号,会跨越高山大洋的距离,穿透语言文字的障碍,被遥远地方的心灵发现和接受。
陆
凡此种种,最终都会通向这样的认识:阅读行为的实质之一,便是发现和建立联系。
这个过程,是一种从不止歇的积累和开辟,仿佛一股水流,从一口泉眼中汩汩涌出,向前流淌,一路上不断有新的水流次第汇入,它们分别来自许多个另外的泉眼。
每一个最初的泉眼,对于阅读者,便是开始时的某一部或某一类读物,它因人而异,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仿佛一个人降生在不同地域,牙牙学语时说的当地的土语方言,但随着他长大成人,就需要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和文字,因此它又总是通往必然性。一个真正的阅读过程也是如此,初始时可以林林总总良莠错杂,但到了某个阶段,便会向着一些世有定论的经典之作进发。这个过程是殊途同归,是万法归一,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阅读中的联系,体现为因果接续的无数次循环,手头的每一本书,都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常常会是此前一本书的结果,又成为后面的一本书的原因。这样的阅读的开展,早晚会接近于一种广阔浑然的境界,就好像大地上众多的河流,在流淌中不断地交融汇集,直到有一天汇聚成为一片浩渺无垠的水面。那是《庄子·秋水》里描绘的场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径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在那样的时候,一个阅读者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澄明之境。那种舒卷自由、毫无拘囿的感觉,借用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名篇《念奴娇·过洞庭》,差可比拟。时近中秋,他月夜泛舟于洞庭湖上,月光云色,倒映在明镜般的浩瀚水面上,欣然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