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非洲文学理念

穆科马小说《肖先生》书封 资料图片

《十全九美》书封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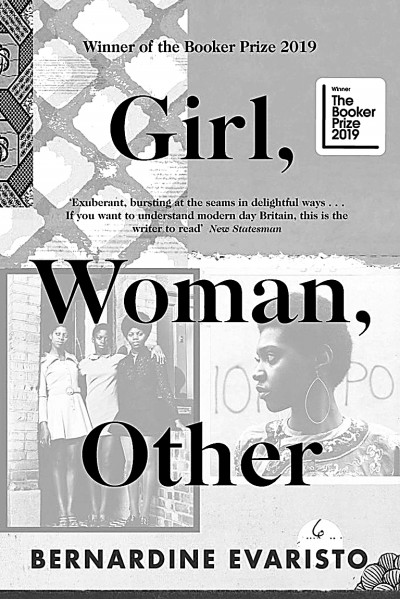
《女孩、女人、其他》书封 资料图片

布奇·埃梅切塔 资料图片
【深度解读】
2021年4月22日,布克奖短名单揭晓。之前呼声较高的长名单候选小说、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戈的小说《十全九美》遗憾未能进入短名单。这部小说是恩古吉用其部族语基库尤语创作、并自己译为英语版的。恩古吉成为首位以非洲本土语言写作获得该奖长名单提名的作家。作为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热门人物,恩古吉出版过多部英文作品,包括《孩子,你别哭》《一粒麦种》《血色花瓣》等小说、自传、戏剧及文学评论等,是非洲现代文学第一代作家群体“马卡雷雷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恩古吉除用英语创作外,还曾用基库尤语创作戏剧《我想结婚时就结婚》和小说《十字架上的魔鬼》。如今这部《十全九美》从某种意义上也再次印证了恩古吉从马卡雷雷作家大会以来对于非洲文学创作理念的坚守。
“马卡雷雷一代”的称呼源自1962年马卡雷雷非洲作家大会的深远影响。他们将非洲现代文学发展的60多年按作家第一部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分为三代,即50~60年代的第一代,也称“马卡雷雷一代”,70~80年代的第二代,以及90年代之后的第三代。尽管有学者指出,这种线性历史分期方式有诸多不严谨之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却能厘清非洲文学发展的概貌以及同时期非洲作家的一些共同诉求。
1.用什么语言写作——争论的焦点
20世纪中期,正逢非洲国家独立运动的顶峰时期,非洲各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以独立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然而殖民统治虽已结束,遗留问题却仍然极大困扰着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去殖民化成为这些国家日趋紧迫的问题之一,而跨越国界的交流与合作在探讨去殖民化的普遍问题上凸显了重要性。对于新独立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家亟待复兴,而手握笔刃的他们也跃跃欲试加入去殖民化的浪潮中。在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看来,积极举办或参与各类国际作家会议、以极大热情投入各种文学实践,是与其他政治活动具有同样效力的斗争方式,用文学表达呼声正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2年7月,在新独立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卡雷雷大学举行了非洲英语文学作家大会,沃莱·索因卡、钦努阿·阿契贝、恩古吉·瓦·提安戈、奥比·瓦里、克里斯托弗·奥基博、兰斯顿·休斯、桑德斯·雷丁等作家、评论家及一些知名出版商悉数出席。会议由南非作家、《非洲形象》的作者艾捷凯尔·姆赫雷雷主持。
此次会议首先讨论的就是语言问题。与会者就如何定义非洲文学展开了激烈讨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否能代表非洲文学?如果那些不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文学算是非洲文学的话,那么作品中的非洲特征该如何识别?是否非洲人书写的文学就是非洲文学?是否一定要书写非洲经验等。
事实上,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一直是非洲文学的焦点问题。南非早在1901年就出现了用本土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也是非洲第一部小说:托马斯·莫夫罗用布索托语创作了《东行旅者》,但直到1931年才出版。索尔·普拉杰于1920年用英语创作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姆胡迪》于1930年出版。到20世纪中期,因殖民地教育及文化政策等多种因素,英语逐渐成为非洲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语言。但围绕非洲文学到底该用本土语言还是欧洲语言写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伊巴丹大学于1959年出版的《非洲文学指南》列出非洲文学有关书目。它按照英语文学作品及非英语文学作品分成两大部分,英语文学作品部分则按照选集、期刊、专题、小说、其他等进行分类,而非英语文学作品下又分为法语区非洲,比属刚果,南非以及西非四部分。这份指南中非洲文学的概念涵盖所有非洲人用任何语言创作的文学,却未得到文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会议讨论中,以恩古吉和瓦里为代表的作家认为,非洲文学必须由非洲语言书写,只有使用本部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才能真正体现本民族的精神,实现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他们对这次会议的名称“非洲英语文学作家大会”提出异议,认为“英语文学”这个限定会把大量用非英语写作的作家排除在外,而且还会默认非洲文学是用英语写作的属性。此外,尽管大会设定英语语言文学的参会门槛,但图图奥拉并未被邀出席这次会议。早在1952年图图奥拉就在欧洲陆续出版了多部英语创作的小说,作品在西方评论界获得诸多好评。瓦里认为,这次大会有意把图图奥拉排除在外,就是因为图图奥拉所使用的英语是不符合这次大会所暗含的殖民教育中推崇的“马卡雷雷式英语”或“伊巴丹式英语”,那是所谓文学创作应该使用的标准英语,而这个标准是由非洲文学的操控者制定的。
恩古吉在1986年发表《思想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学语言的政治》中进一步阐述其思想:“子弹是征服肉体的手段,语言是精神征服的手段”,如果非洲文学用英语书写,那么英殖民者对非洲各国的精神奴役就永不会结束。正因为如此,恩古吉从1978年起决定改用基库尤语写作。同时他宣布放弃原来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名字詹姆斯·T·恩古吉,而改为基库尤语的名字恩古吉·瓦·提安戈。恩古吉改名的同一年,马卡雷雷大会主持人、南非作家艾捷凯尔·姆赫雷雷也为了支持本族传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带有本部族色彩的艾斯克亚·姆赫雷雷。
以阿契贝为代表的另一派作家则认为,对作家本人来说,如果英语能够承载其非洲经历,则使用英语书写无可非议,但这个英语绝非“大写的英语”,而是注入了新的元素,是改变后能适应非洲环境的新英语。阿契贝在1965年发表论文《英语与非洲作家》再次阐释其观点,不应该把非洲文学塞进一个简单的定义里。非洲文学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由能够反映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学与能表达各个不同文化的部族文学构成。任何忽视了非洲的复杂性而对非洲文学进行定义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马卡雷雷作家大会的两派观点一直延续到后马卡雷雷时代。第三代作家阿迪契亚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的写作语言是英语,除非出于情感原因,否则用其本部族语伊博语写作是不切实际的。恩古吉·瓦·提安戈的儿子、康奈尔大学文学与非洲研究助理教授穆科马·瓦·恩古吉则表示,后马卡雷雷一代作家“在英国形而上意识形态体系内思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以至于无法看到这种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扭曲违背了他们的世界观。”对于一些作家来说,“非洲文学仅始于1957年出版的《瓦解》。即使当时有那些为非洲本土语言争取权利的作家,后来也只能用英语写作。”
正如非洲研究学者蒋晖所言,“因为非洲文学研究的二律背反,非洲文学的语言之争60多年仍未有定论。”但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作家和机构在积极探索,以改变非洲文学用西方语言创作一枝独秀的局面。
非洲作家比瓦斯戈耶·伯瓦姆维斯基尔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的文学是否有未来?》中通过一系列事实的分析,提出非洲本土语言发展的乐观前景。在他的分析中,不仅非洲作家个人,而且各类机构及团体也在努力探索非洲文学中的问题。
2014年,凯恩非洲文学奖的经理利兹·阿特里和穆科马·瓦·恩古吉共同创立了姆巴蒂-康奈尔斯瓦希里文学奖。这是第一次专门为非洲语言写作设立的奖项。获奖作品将获得1.5万美元的现金奖励,并有机会由坦桑尼亚的姆库基纳·恩尤塔出版社和肯尼亚的东非教育出版社出版斯瓦希里语版,由非洲诗歌图书基金出版英文版。
2015年2月,曾出版过多部英文作品的尼日利亚出版社“木薯共和国”出版了一部电子版多语种短篇小说选集。选集中大部分故事由英语译为不同非洲本土语。如楚玛·恩沃科洛的《鱼》被译为皮钦语,宾雅瓦格·瓦纳依娜的《被封印的念头》被译为斯瓦希里语,萨拉·拉迪波·马尼卡的《穿橙色衣服的女人》被译为约鲁巴语,托尼·凯的《子叶》被译为伊博语,阿布巴卡·亚当·伊巴尔汗的《涂画的爱》被译为豪萨语等等。艾沃尔·哈特曼发表在贾拉达非洲未来选集上的短篇小说《最后一涌》被译为斯瓦希里语。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用本土语言出版的非洲文学实践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是对非洲文学边界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通过出版类型小说以打破正统小说的边框,而且还跨越了语言的界限,证明类型小说可以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出版,并进入主流文学视野。
2.主题与审美——一言难尽的困惑
事实上,马卡雷雷会议的语言之争并非最主要的焦点,非洲文学的主题与审美是更激烈的争论议题。根据马卡雷雷会议纪要显示,作家们对非洲文学的主题叙事与审美模式进行了热烈讨论。
克里斯托弗·奥基博认为,非洲文学必须深深扎根于非洲的土壤,必须从非洲的经验中诞生,必须与非洲的情感一起搏动。简而言之,非洲文学之所以成为非洲文学,是因为其表达了非洲特有的精神,是桑戈尔和塞萨尔最先感受到并表达出来的黑人性。如果缺失了这种黑人性,即使是非洲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能称之为非洲文学。但有其他作家反驳说,过分强调黑人性,容易导致文学的公共性倾向,文学会沦为对黑人境况浪漫的诗性描述,而非作家彼时彼地独特而个性的体验。事实上,对黑人性的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前法属殖民地作家和前英属殖民地作家之间。而之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声音,则部分归因于英法两国不同的殖民教育政策。法国在非洲殖民地施行完全同化政策,而英国则施行分而治之的间接统治政策。因此,来自前法属殖民地的作家始终高举黑人性的旗帜,以帮助确定自己的主体身份认同,而来自前英属殖民地的作家则更倾向于坚守本部族的传统特性。姆赫雷雷坚持认为,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相同,因此,黑人性不能被当作是治疗非洲所有文化弊病的理想药方。非洲作家能做的而且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书写方式扭转西方对非洲文学的固有印象。
当时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非洲文学应该具有非洲特征。这种特征其实是西方对非洲的刻板印象。费伯费伯出版社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陆续出版了图图奥拉的几部小说。出版社认为图图奥拉的小说充满异域风情,语言虽然破碎,但与浓厚的非洲背景相得益彰。正如编辑艾伦·普林格尔给图图奥拉的回信中说:“你小说中的语言虽然不是非常符合传统的标准英语,但正因此,你的小说才充满魅力。我们认为如果使它符合标准英语的语法和拼写规则,那么对作品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就像只有西非人才会有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一样,你的写作风格充满魅力。”但图图奥拉的作品却受到非洲本土评论家的指责。他们认为,费伯费伯出版社故意不去纠正图图奥拉的拼写错误及语法就是为了让小说看起来更具有异国情调,更符合他们对 “非洲”的偏见,而图图奥拉的小说只会加固西方世界对非洲文学的这种固有偏见。这对作家个人和整个非洲文学事业都是巨大的危险,会阻碍非洲文学的正常发展,最终让非洲文学沦为无法凭借真正的文学价值走向世界的伪文学。
对于非洲文学表达的主题,一些作家认为,在欧美文学占据主导的当下,如果非洲文学不合拍就会跟不上潮流。奥比·瓦里则担心当下非洲文学所理解和实践的现状无论从语言、主题还是审美,其实与传统欧美文学的标准完全一致。这样发展下去的非洲文学注定只是欧美主流文学的一个小附属品。
尽管有争议,但作家们都认同非洲文学应该与非洲人自己的独特经历和情感有关,殖民屈辱、挫折、悲伤、痛苦、仇恨、反抗、报复、兴奋、喜悦、爱,这些经历赋予非洲人独有的特征。此外展现非洲传统和西方之间冲突的主题也同样重要。在文学去殖民化过程中,作家应该坚定文学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立场,而不应该超然于客观现实之外。
3.面向未来——不变的非洲主体意识
可以说,马卡雷雷非洲作家大会极具开拓意义。恩古吉于2013年再次回到马卡雷雷大学演讲时说,当时的大会激发了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洲现代作家的写作风格。非洲文学从这次大会后开始呈现规模化发展,仅海涅曼教育图书出版公司推出的非洲作家系列就陆续出版了300多部非洲文学作品。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推出了“三个皇冠”非洲文学系列丛书,主要出版非洲戏剧。其他出版社也都积极寻求和非洲作家的合作,非洲作家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不仅仅是非洲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会议上作家们极富洞见的诉求也极大影响了后马卡雷雷时代非洲作家的文学创作实践。
2012年7月马卡雷雷大学文学系再次举办非洲文学会议,纪念1962年首届大会举办50周年,同时反思自首届大会以来当代非洲文学研究中出现或潜在的新问题,以明确非洲文学发展的方向。
2017年10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巴黎举行盛会,纪念马卡雷雷首届非洲作家大会55周年。并于会后出版了以首届作家大会的合照作为封面的《赐予礼物的众神:非洲短篇故事集》。
相较于第一代非洲作家的群体构成,第二代作家中女性作家渐露锋芒。除承续前一代作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外,第二代作家开始关注非洲流散群体。泽纳布·阿利的《死胎》和《善良的女人》,布奇·埃梅切塔的《二等公民》《在沟底》《为母之乐》等也都引起广泛关注。
第三代作家包括阿迪契亚、苏伊·戴维斯·奥昆博瓦、穆科马·瓦·恩古吉、贝纳丁·埃瓦里斯托等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作品从题材到形式都异常丰富。阿迪契亚的三部小说《美国佬》《紫木槿》《半轮黄日》充分展示了种族议题与性别议题的重叠。穆科马的《歌中永生》被称作“一封献给非洲音乐、歌曲的优美情书”。苏伊·戴维斯·奥昆博瓦在他的奇幻小说《风暴之子》和《寻神者》中,以充满矛盾的时空想象拓宽了非洲文学的写作边界。阿德索坎的《天空之根》就情节的原创性而言可被称为非洲版《百年孤独》。贝纳丁·埃瓦里斯托的小说《女孩、女人、其他》曾获2019年布克奖,连续五周蝉联2020年英国平装小说排行榜榜首,连续40周位列畅销榜前十,今年又入围2021年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这部小说讲述了一百多年间生活在英国的12个不同年龄、兴趣及社会文化背景黑人女性的个人经历。候选名单的评审们认为:“这是一本由自身独特的能量驱动的伟大的作品——它将小说的形式推向了一个新颖而令人振奋的方向……这是一位优秀作家在讲述故事方面的壮举,生动地传达了当代英国跨时代黑人女性的声音。”
纵观最近60多年非洲文学的发展,新生代作家不断崛起,就像当年马卡雷雷一代作家一样,他们仍然在非洲文学的未来之路上积极探索。本世纪已连续举办了三届非洲作家大会,2021年即将迎来第四届非洲作家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非洲文学的未来”与前三届的主题“非洲身份”(2020年)、“非洲文学中的文化成见”(2019年)和“重新想象非洲文学”(2018年)似都在回应着60多年来作家的思考与诉求。也许会议征稿要求里“只接受英语创作文学”的标注表达出要将语言问题暂时搁置,而将重点放在思考如何以更明确的非洲主体身份使非洲文学跻身世界文学空间的愿望,而这也是非洲作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祈盼。
(作者:蒋春生,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物资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